
古驿道,也称驿道,是指古代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人员往来的通路,包括水路和陆路,分为官道和民间古道。古驿道上每隔五里设置一阁(墩),十里设置一亭(铺),三十里设置一驿,驿驿相接,纵横网络,以京师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古驿道既是历史上一个地区对外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又是当地历史发展的重要缩影和文化脉络的延续。

池河古驿道位于京京古道(南京-北京)上,亦称北京至南京大道,南北走向,始建于五代,兴盛于明清。是古时南京到北京陆路的必由之路。朱元璋称帝后,为传递信件和军事需要,正式开辟南京至北京大道,全长约1500公里。经滁州境内全长约129公里;经定远31公里;经现池河镇约22公里。定远境内京京古道沿途铺递有黄练铺、崇家铺、刘家铺、山沟铺、枪峰铺、岱山铺,东接滁州;据《中都志》载每铺正房3间、东西厢房各3间,邮亭1座,门房1间。定远境内京京古道沿途仅有池河驿,明朝时期,北接凤阳濠梁水马驿,东至滁州大柳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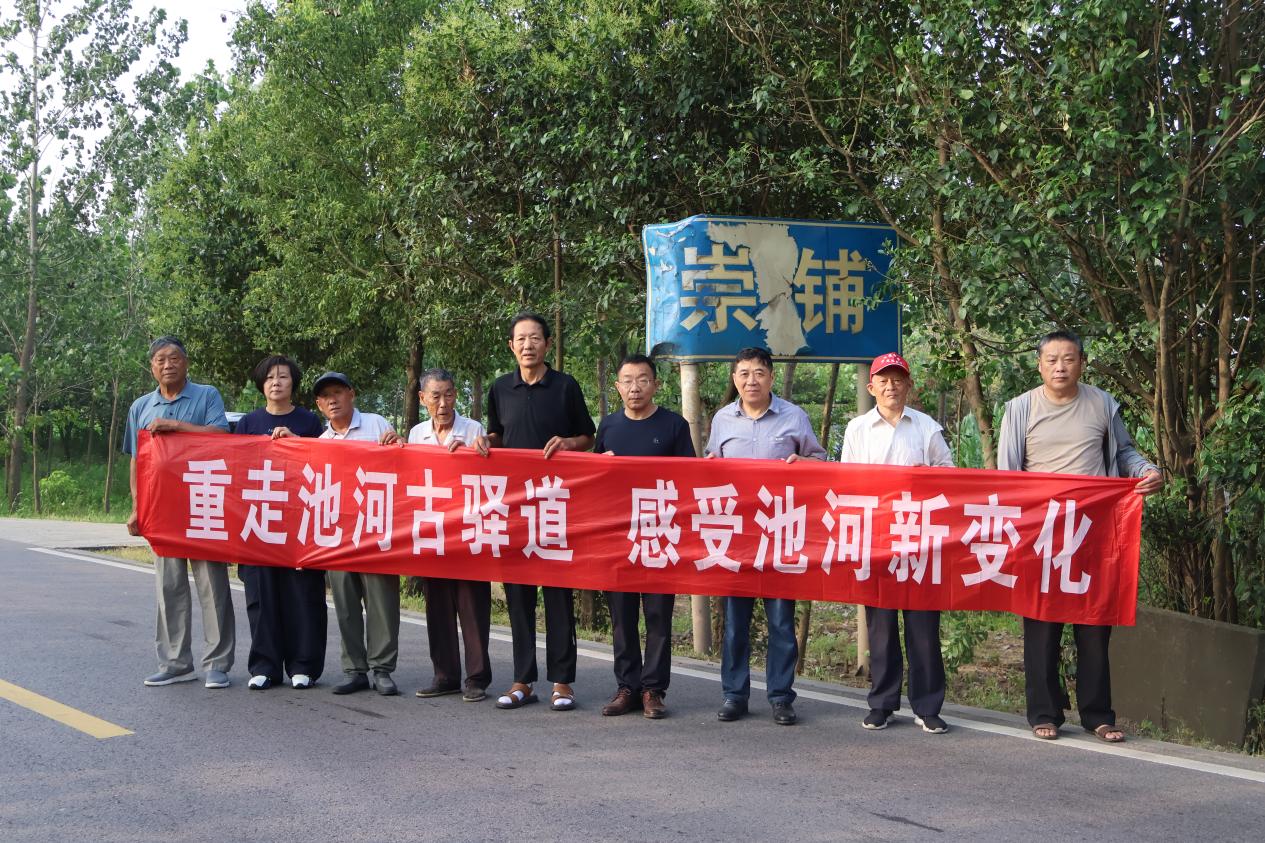
池河驿,在今安徽定远县东池河南岸,以临池河得名,古为驿站。设立于汉代,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清置巡司于此。明清时期,池河驿位于北京至南京的官道上,是历史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千百年来无数官商行旅车行马经过这里,也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诗篇。历史见证了“池河驿”依山傍水、环境优雅、关锁通衢、交通便捷、商贸云集、繁荣昌盛、悠久历史、建筑规模宏大、位置之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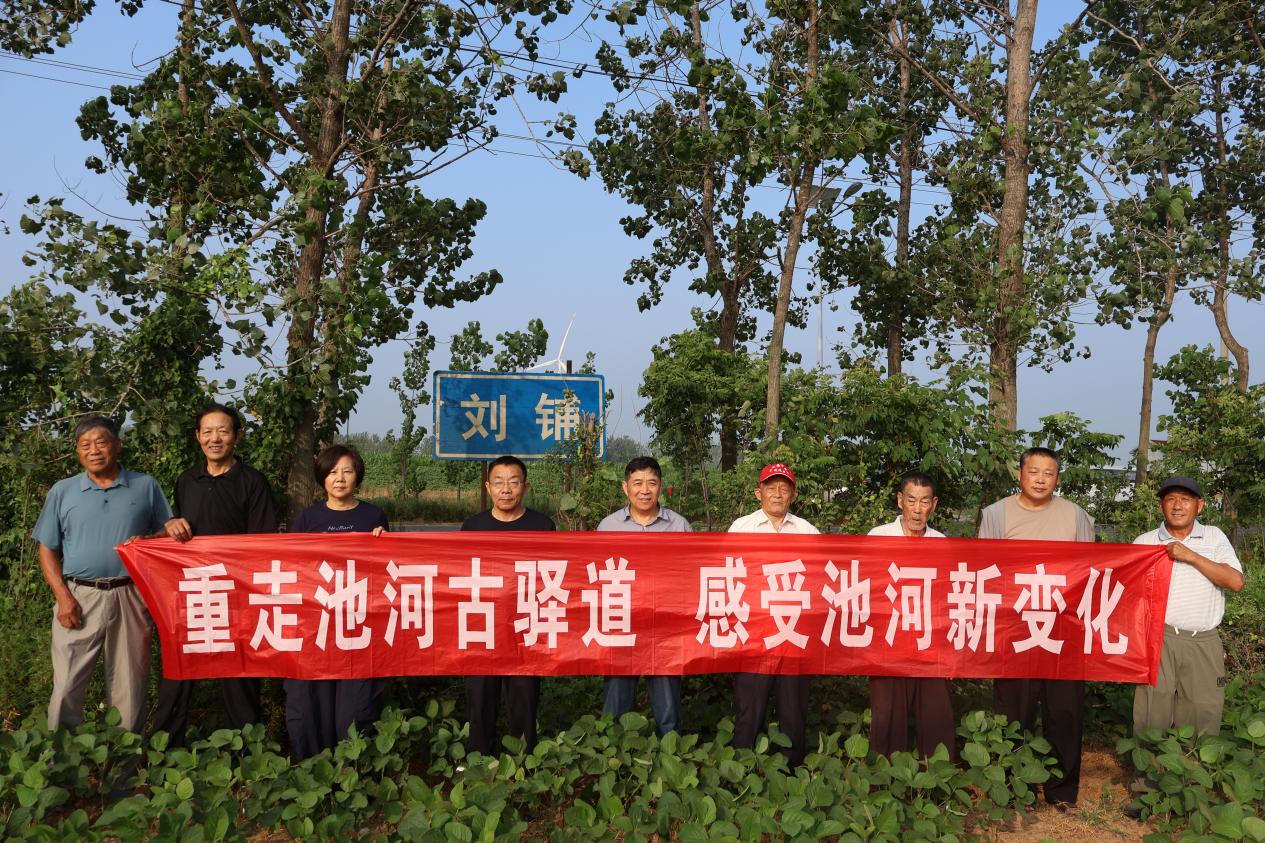
池河驿,是明代凤阳府至南京的官方最重要驿道之一,这条驿道由凤阳县的二铺、总铺、黄泥铺,到定远县的练铺、池河驿、大柳树驿,穿越滁州清流关到滁阳驿,再经江浦县浦子口,渡江到南京,全程330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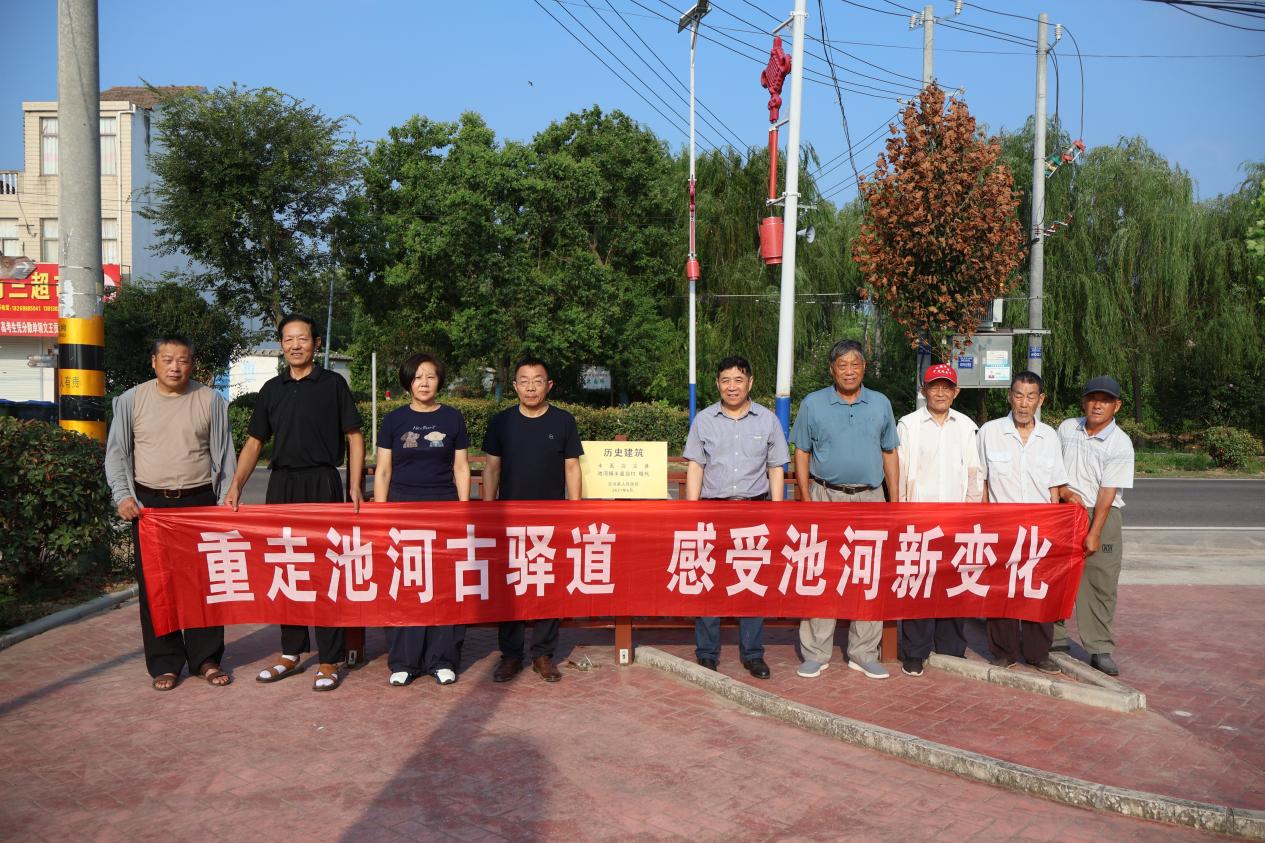
明成祖朱棣称帝后,于1402年12月18日决定迁都北京。设立京京官道,其基础是燕陵古道,它北自燕京(今北京)起始,经河北、山东、皖北抵淮河,在临淮关渡淮河后向东南经总铺、黄泥铺、红心驿、练铺、池河驿、大柳驿、广武卫、清流关至滁城,出城后经担子铺、官塘铺(乌衣)过滁河至江浦县境内,渡江后抵达金陵(今南京)。

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宋濂在《游涂荆二山记》中描述了他曾经来过池河驿:濂既游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驿,适邮卒递内使监公牒至。
清代学者戴名世经过此道,曾描绘:“过磨盘山,山势峻峭。重盘曲,故名。为滁州要害地。”

7月9日,定远县池河镇组织开展“重走池河古驿道,感受池河新变化”活动,沿池河古驿道线路,从红心镇和练铺交界处出发,一路向东南行进,直抵至磨盘山的池河镇和大柳镇交界处终点。历时两天,行程52公里。红心镇和练铺交界处至池河镇玉皇阁原先古驿道已修建成宽阔的水泥、柏油路面,路面虽平坦,但已没有了原古驿道的模样;玉皇阁至磨盘山段,经过岁月的催残和地方发展的变迁,路段已破坏的面目全非,荡然无存,只能在老人指引下,摸索前行,一路上路障多多;昔日的三岔河现已建成岱山水库,只好绕道进入老岱山铺地界,除了驿站、峰堠遗址、驿道,还可看到保存完好的古迹是数百年的岱山铺古井,修建的一座石桥在杂草丛生中清晰可见。草丛中,残碑断石依稀可见,仅此而已,再无当年供“铺吏”或“铺兵”居住和饲养“铺马”备用的茶亭或驿房及四周围墙的建筑,曾经纵横交错的十字路上,昔日往来的车马,人马沸腾,马蹄声声,商贾云集,早已没有踪影。

随着历史的变迁,现在古驿道已丧失了它的功能,但它是池河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史实和动人故事,有着池河地理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饮食文化、抗战文化等深厚的历史积淀。

重走池河古驿道活动紧贴京京古驿道定远段全长31公里的沿线行走,主要涉及练铺、池河2个乡镇16个村庄、4个街道、6个美好乡村、2个水库及岱山山峰等。
沿途看到了311省道、明巢高速公路、京沪和合新高速铁路疾驰的列车与汽车;看到了半面店古井、施茶痷古井、池河太平桥、马号巷、七里河古桥、岱山铺古井及曾经辉煌的晓山寺旁的一棵硕大的古银杏树保护完好;看到了青岗、刘铺、半面店、七里河、岱山新村美丽乡村和金湾体育生态公园及岱山小苑的巨变,从交通、乡村变化、农文旅深度融合、工业迅猛发展和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中更是切身感受到池河在飞速发展,不断超越。

通过实地调查、挖掘史料、梳理文脉、走访专家和当地群众,在追寻古人留下的足迹中穿越历史、见证辉煌,在古今对比中触摸沧桑、感悟变革。展现池河古驿道沿途村庄在和美乡村建设中的新气象、新作为、新故事。旨在挖掘历史文脉,传承池河历史文化,展示池河古驿道沿线当今变化,在南京都市圈实现资源共享,强化人文认同,激发共同发展的内生动力,助推池河农文旅建设。(李学兵)










17531e11-b74b-424c-9cfd-b7c6a79f94d1.jpg)



766eaf13-f0ed-4d51-81a0-00930fa6376c.jpg)







